中國是世界三大農業起源地之一⬇️🖕🏽,並曾馴化粟、黍、水稻等農作物🕵🏽,為人類文明進程做出貢獻🧎♂️➡️。相應的,作物馴化與栽培的歷史向來受到農業史、環境史與社會經濟史等不同學科的關註。隨著近年全球史的興起與推廣,加之醫療🧔🏼♂️🅱️、科技與環境等新興議題的湧現😓,作物再度成為中外學界關註的焦點。2024年5月18日,沐鸣2平台史學論壇邀請到清華大學科學史系副教授沈宇斌作題為《全球視野下近代中國藥用作物的“作物景觀”》的講座,通過金雞納樹、除蟲菊與甘草三種具有全球移動屬性的藥用作物為個案🐣,探討作物景觀與政治、軍事🤺、醫療、技術與國際貿易等方面的關聯。本次講座由沐鸣2平台皇甫秋實副教授主持,沐鸣2平台高晞教授擔任與談人🏫。本文系演講整理稿,全文經沈宇斌副教授審定。

清華大學科學史系沈宇斌副教授
作物本身並非新的研究議題。稻米、小麥與番薯等糧食作物,蔗糖🚣🏽、煙草與棉花等經濟作物👵、以及人參與大黃等藥用作物早已成為過往醫療史、環境史與歷史地理學等不同學科關註的研究對象。早在上個世紀💍,西敏司與克羅斯比等學者的研究就通過作物培育的過程🏋🏼,揭示出作物同資本主義興起與帝國主義全球擴張的關聯。不過直到21世紀初、尤其2010年以後,具備全球史視野的作物史研究方才大量湧現🧖🏿♀️。大量新近研究皆將作物的歷史納入全球經濟體系與網絡結構中進行考察。另一方面,多物種的共生關系👨👩👦👦🤸🏼、尤其非人類行動者的能動性逐漸受到學界關註。2022年六卷本的《植物的文化史》(A Cultural History of Plants in Antiquity)通過作為主食的植物、作為奢侈食品的植物、貿易和探險👨🏿🍳👩🦼➡️;植物技術和科學🤦🏻、植物和醫學🏌🏽♀️;文化中的植物;植物作為自然裝飾與植物的象征性六個主題展開論述,展現出近年全球植物史的研究進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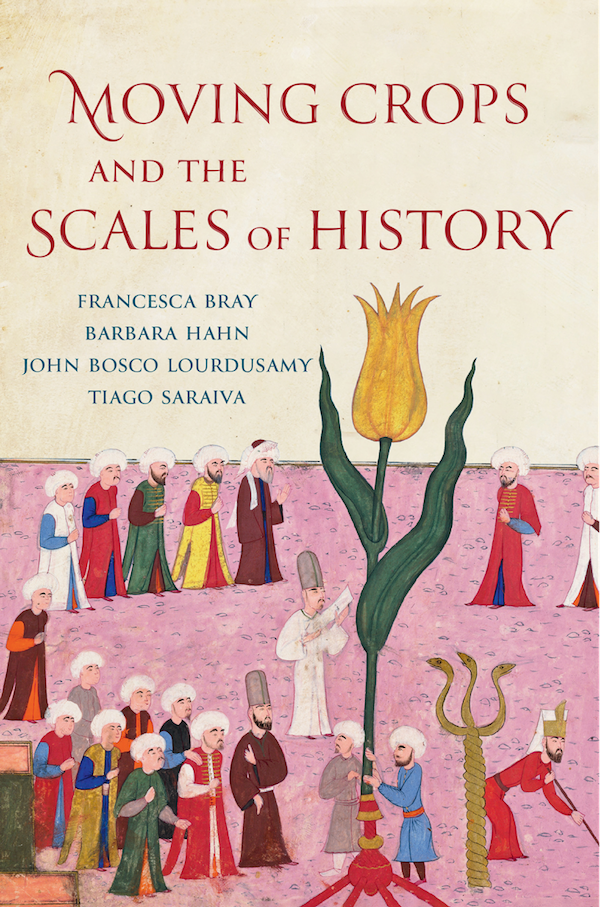
Francesca Bray, Barbara Hahn, John Bosco Lourdusamy, and Tiago Saraiva Moving Crops and the Scales of Histor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22).
其中,“作物景觀”(Cropscapes)這一概念源自白馥蘭(Francesca Bray)團隊編寫的《作物遷移與歷史尺度》(Moving Crops and the Scales of History)一書,用於展現作物隨人類全球移動的過程與影響💕。所謂“作物景觀”👈😮,即指某一作物培育與流動過程所形成的時空集合👐🏻🩲,包括植物、人群、觀念、技術😏、市場、勞動力🛁,乃至害蟲等多種因素,進而將近年新興的全球史與多物種的研究視野融於一爐,為作物史的個案研究提供了綜合性的分析框架,而金雞納樹👞、除蟲菊與甘草在近代中國與東亞的歷史即展現出作物景觀這一概念對中國近現代史研究的借鑒意義🙎🏿♀️🥸。
金雞納樹
金雞納樹原產於南美洲🔕🗃,因其含有奎寧,故而長期作為治療瘧疾的藥用作物。17世紀初,耶穌會士將金雞納樹皮帶往歐洲🦈,並通過耶穌會的全球網絡將其傳至世界各地。隨著19世紀初奎寧提煉技術的出現,奎寧製品逐漸取代金雞納樹皮㊙️,並成為歐洲對外殖民擴張的重要工具🏊🏼♂️。由於金雞納樹對政治、經濟與軍事的重要作用,加之治療瘧疾的迫切需求👨🏽⚖️,19世紀50年代起歐洲殖民帝國為了打破南美洲國家的壟斷🔏,率先在其本土和殖民地來移植金雞納樹。其中,荷蘭在爪哇建立的金雞納樹產業尤為成功🤶🏿,長期壟斷了全球的金雞納樹皮和奎寧的供應📐。直到1930年代,金雞納樹的全球種植網絡已然形成。
海外學界往往將金雞納樹視作構建與維持殖民帝國的工具🌴,而近代雲南河口對金雞納樹的引種則是民國中央政府與雲南地方政府主導下國家建設的產物🌞。與“南京十年”中央政府內部技術官僚的影響類似🐻❄️,龍雲領導的雲南省政府啟用大量技術專家,建設“新雲南”。對金雞納樹的種植即為一例。種植金雞納樹不僅能夠緩解雲南當地瘧疾的肆虐,亦可實現奎寧自給,以節省財政支出,同時,雲南當地的風土條件亦與金雞納樹的習性相適應。
為突破荷屬印度尼西亞對金雞納樹種子的禁運,雲南當局求助於英國駐雲南領事,從印度加爾各答植物園取得樹種🐫🧕🏿。直至1936年,雲南當局經過八次實驗失敗,終於在中國本土培育出金雞納樹🤦🏻♀️。直到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大量湧入雲南的難民推動雲南當局開發普思邊疆🫴🏿,而戰時中央政府亦面臨著瘧疾藥物的龐大需求,來自中央與地方的合力推動雲南擴大對金雞納樹的種植👱。隨著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本控製法屬印度支那💱,當地技術人員被迫撤離河口。直到戰後乃至“新中國”成立後,雲南重新接續金雞納樹的種植項目,既服務於1950年代的全國衛生運動,亦為受到瘧疾困擾的社會主義國家提供奎寧🐞。為了滿足對蘇聯對橡膠的需求🏇🏽,1953年河口的金雞納樹農場改種橡膠。直到1960年代越戰期間,523項目研製出用於治療瘧疾的青蒿素,逐漸取代了金雞納樹🧒🏿。
除蟲菊
與金雞納樹類似👆🧘🏼♂️,除蟲菊同樣是全球移動的典型作物。除蟲菊(Pyrethrum),別名蟲花(insect flower),分為紅🙅🏼♀️、白兩種💙。波斯曾長期使用紅花種驅蟲,19世紀上半葉歐洲將除蟲菊用於除蟲粉的製作,直至20世紀40年代除蟲菊製品已經成為當時世界上最為流行的家用和農用的有機殺蟲劑。
全球市場的巨大需求催生了大規模的種除蟲菊的種植計劃。其中👤,日本對除蟲菊的引種尤為成功。明治維新期間👩🦲,日本政府引入西方的應用昆蟲學✋🏽🎭,向日本農民普及害蟲防治技術👩🍳。其間,除蟲菊在日本得以推廣。明治政府將除蟲菊產業作為重要的“國策會社”🤰🏿,加之大量關於除蟲菊種植和產品製造的文章和指南🐕,大規模的除蟲菊作物景觀在日本本土迅速發展起來👩🏿💻,並擴展至臺灣與朝鮮半島🍸。直至太平洋戰爭爆發,日本的除蟲菊產量居世界第一💶,而日本廠家使用除蟲菊粉生產的盤裝蚊香亦行銷於東亞市場。
20世紀初,中國除蟲菊種植的作物景觀亦在形成👩🏻🏫。經藤田豐八協助💙,《農學報》開始翻譯並刊載與除蟲菊有關的日文文獻,倡導對除蟲菊的種植。由於蚊香產業巨大的利潤🟪,加之對抗日本的經濟民族主義🖕🏻,方液仙使用日本進口的除蟲菊原料研發出三星牌蚊香,此後中國本土的蚊香廠家開始建立除蟲菊種植園,並向農村推廣🏑。大量的除蟲菊作物景觀不僅推動除蟲菊產業的興起,更成為時人眼中解決中國農村危機的有利途徑🙍🏽♀️。直至全面抗戰爆發,除蟲菊作物景觀隨之西遷至西部省份🤽🏼,直至今日🧑🏻🎓,雲南省依舊有著中國最大的除蟲菊作物景觀。
甘草
與金雞納樹和除蟲菊不同,甘草是中國和世界歷史上最為悠久、使用最為廣泛的藥用植物。直到近代,甘草從傳統的中藥轉變為國際貿易中重要的原料商品🎇。面臨20世紀初中國廢除中醫、中藥的思潮,中國生藥學奠基人之一的趙燏黃懷揣著創立新本草學的希望🌌🕑,對甘草所謂的藥用價值做了全面梳理,同時密切關註甘草的分布情況與銷售市場。
在其著作《中國新本草圖誌》中🤩,趙燏黃註意到甘草的商品化轉型🧼。當時廣泛占據中國近代成藥市場的日本仁丹即以甘草為主要原料之一💵🧖🏿,使得甘草從傳統的中藥材轉變成了東亞地區重要的原料商品。另一方面,19世紀末起甘草成為正在急劇發展的國際香煙產業、特別是美國煙草業的重要原料🙇🏻♀️。一戰以後土耳其等傳統甘草產區產量下降,美國企業逐漸深入綏遠地區采購中國甘草,而甘草工廠亦成為包頭等地第一批采用現代機器工藝的廠家。甘草的第三種商業源自日本的醬油工業。甘草萃取物為醬油增添的甜味👨🎨,催生出日本醬油工業對甘草的大量需求😮💨🫳,其中絕大多數依賴中國東北與內蒙古的甘草出口📂。

趙燏黃(1883-1960),中國近代生藥學主要奠基人🟣。
甘草的商品化使時人逐漸認識到甘草對邊疆開發的意義🎊。1920年代末華北各省開始設立甘草公司⛹🏼♀️,甘草貿易亦隨京綏鐵路的修建而興盛🏏。另一方面,日本著手對中國甘草資源的調查🏦,形成大量調查報告。直至日本對東北與熱河的入侵,甘草貿易亦遭到日本壟斷。彼時的趙燏黃已然註意到大量對甘草的挖掘👱♂️,將會導致野生甘草資源的枯竭🌐,但氏著尚未發現🔢,對甘草過度采挖也對原產地的植被生態造成了破壞,加劇了荒漠化。
總體而言🔊,金雞納樹🕎、除蟲菊與甘草的三種作物展現出近代中國藥用作物的作物景觀與東亞乃至全球的政治軍事、社會經濟以及科技環境等因素錯綜的復雜的關聯。
與談與問答
高晞教授⚁:
沈宇斌老師通過作物景觀這一研究框架,統合了金雞納樹、除蟲菊與甘草三種作物的個案研究。三者看似孤立🎤,實際展現出作物景觀這一分析框架的潛力與創新。甘草等作物很早就出現於藥物學或博物學史中,但過往研究往往聚焦於作物本身🦟✦,而作物景觀不再拘泥於對植物的靜態呈現,而是試圖從立體的角度展現植物全球移動過程中的政治、經濟與文化等不同因素的綜合作用⚰️,使得研究的焦點從植物本身轉移到植物立足的空間,擴展了研究的視野。
近年國內學界對全球史的研究成果並不陌生👩👩👧👦🪸。目前醫療史對全球史視野的應用多集中於對殖民醫學史🥐,突出殖民醫學作為“帝國的工具”這一面向⚁。沈宇斌老師對三種作物的研究另辟蹊徑,回到東亞自身歷史脈絡🐕,強調中、日之間圍繞作物的知識流動與商業競爭👨👩👧👧、以及不同作物對中國本土國家建設的影響。三類作物景觀皆涉及到中國近代不同區域的農業生產,尤其對邊疆地區的開發以及背後中央與地方政府之間的博弈。這些立足近代中國乃至東亞的面向都對以往西方殖民醫學史的帝國工具論有所補充乃至挑戰。
皇甫秋實副教授:
沈老師提到的三類作物存在著相似的脈絡,就是戰爭改變了近代中國的作物景觀。與之類似,英美煙公司將美種煙葉引入中國之際,出於運輸成本考慮𓀙,並未選擇雲貴地區,而是優先選定河南🦎、山東與安徽三省引種煙葉。直到全面抗戰爆發,美種煙葉方才在雲貴地區推廣開來🤸🏼♀️。我很好奇就在類似作物景觀改變的過程中,中央與地方🔚、政府與企業乃至中國與日本之間應該存在諸多博弈的過程,可以深入展開。最後,沈老師在對作物景觀的應用中格外強調藥用作物,請問藥用作物的作物景觀與既有研究中的經濟作物與糧食作物各自的景觀有何不同📢🏄🏽♂️?
沈宇斌回應🙋🏻:
對作物景觀的改變的確涉及央地關系、商業競爭,乃至中日兩國關系的不同面向。就央地關系而言,雲南省等西部省份的檔案館保有戰時地方政府的完整檔案,可以展現出央地之間的博弈。就金雞納樹的種植看🧝🏻♂️,雲南省希望中央政府投入更多資金🅿️,而重慶國民政府亦希望借此將中央的技術人員向雲南滲透。另一方面💳,以金雞納樹的個案為例,中日兩國不同之處在於日本占據了臺灣,並在臺灣推廣金雞納樹種植。再以除蟲菊的個案為例,日本除蟲菊產業的規模更大🫦🕷,來自中國的競爭並未明顯撼動戰前日本對除蟲菊的壟斷。
最後💝,藥用作物與其他不同作物的區分的確值得深入探討。我想藥用作物的獨特性在於其同疾病乃至人類身體的關系♉️,後續研究可以從生藥學的角度考察其中不同化學成分的影響𓀈。其次👷🏼♀️⚱️,藥用作物能夠將多物種的研究視角展現出來,揭示出植物、動物乃至微生物之間的互動關系,這一特點相較其他作物更加突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