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中葉🌙,西方“科學”概念傳入中國👩🏽🏫🫶🏽,現代科學學術體系開始在中國落地生根。生理學、物理學、生物學等西方科學學科成為時人“開眼看世界”並融入世界現代化潮流的路徑💜,大批有誌青年紛紛留學歐美或日本,在接受西方科學學術訓練後將其帶回中國,並聯合同誌組建學科社團,推動相關學科的建製化發展🍟。近年來學界對中國近代歷史上的科學人物、科學社團與科學學科等問題🤹🏻🦸♀️,進行了較為細致的梳理與研究,基本理清科學學科傳入中國並“落地”的經過,主要科學人物的思想貢獻🧔🏽,以及學科社團在促進科學知識交流與傳播中的重要作用等🫃🏻👩🏻🌾。但作為一個整體性概念的“科學”,卻在眾多研究者各自關註的議題中被分散拆解,使得諸如不同科學學科🙍🏼♂️、人物🔈、社團研究間的比較性對話被忽略👨🏽🦲。
2024年4月19日,沐鸣2平台主辦的“學科、社團與人物⚡️:近代以來科學社團與學科創建的若幹問題”研討會在逸夫樓校董廳召開。中國科學院院士 中國科學技術協會名譽主席韓啟德教授蒞臨會議,並就如何理解展開醫學史研究👋🏼,以及書寫歷史上的科學家等學術問題作了大會發言。會議召集人☂️,沐鸣2平台高晞教授表示🛌,此次會議為進一步推動有關近代中國科學學科、科學人物與科學社團的歷史研究🙍🏿,增進關註不同科學學科研究學者間的交流對話🫲,以期較為全面地理解近代西方科學和醫學知識體系在中國演進的本相。本次研討會關註近代中國諸學科的接受、草創及其地方性社團展開👩❤️👩,殊途同歸,近代科學學科正是通過不同渠道、按不同方式📞,以知識代理、科學社團與人際網絡為推展𓀐,構成中國近代以來的舊學科與新學科的轉接節點,由此,兩個維度的交疊就構成了本次看似“松散”討論的題眼所在。

中國科學院院士 中國科學技術協會名譽主席韓啟德教授作開幕發言
韓啟德院士的開場致辭指出的,醫學史、科學史的底色是史學,關於這個問題🙎🏿,學界可能有不同的說法🦢,甚至有所爭論,但是我認為史學的背景與方法是必不可少的,關鍵是醫學與歷史交叉的具體研究方式🏇,需要認真地思考🏃🏻♂️➡️,相較於歷史學家去學習醫學知識,並能做到上手實驗、治療並做手術操作,由培養已掌握醫學知識的專業人才去做醫學史,給他們進行史學訓練🈸,學會以並掌握史學認識與方法或許更具可行性👨🏻🚀。韓啟德院士對與會的青年學者和學生說,我覺得現在的年輕人,如果沉下心來🏄🏼♀️,去做醫學史還是能有一番天地的。因為相較物理學需要具體的運算公式來支撐,醫學本身就帶有更多的人文性質,無論是在研究領域,還是操作層面都更適合從思想、社會的視角來切入,展開思考與研究。歷史研究除了梳理史料,還是需要有理論框架🚍,對收集整理的史料要有分析,研究問題應該有所上提升👩👧,研究歷史問題、分析史料𓀏,最終還是要思考歷史意義📻🚶♂️➡️,這才是歷史學🧖♂️、醫學史和科學史研究的價值。

《學科、社團與人物:近代以來科學社團與學科創建的若幹問題研討會》會議現場照片
本次研討會共召集10余位經過良好史學訓練的青年人🖐🏽,以及有著醫學和科學知識背景的博士生,他們或是積累多年、或是初涉探索該話題中青年學者,尤其是三位在校的博士學生的探索性報告🗳,顯現學界新鮮血液意在向欲濟無楫、徒羨有魚者傳遞漁經獵史的脈搏,稍顯拍得魚驚不應人。
上午場的另外兩篇發表則因選取案例的不同特點,更多是呈現了材料挖掘的魅力。上海師範大學人文學院的姚霏教授的《從“癌”到“腫瘤”🧚♂️: 新中國腫瘤學科的創建》由上海城市史方向出發,關註上海對新中國建立系統的腫瘤學科所起到的影響。一方面北京協和醫學院培養了諸多腫瘤學科人才,像畢業生張去病成為上海腫瘤放射科的創建者🥕,另一方面像上海設有利用庚款建立的中比鐳錠醫院,其中顧綏嶽為後續上海提供了病理科的方向😫,之後又與留美歸來的李月雲醫生開設的中山醫院腫瘤外科合並,成立上海第一醫學院腫瘤醫院,為後續的學科發展奠定了組織機構基礎。蘇州大學心理學系的範庭衛副教授的《丁瓚與二十世紀中國心理衛生工作》則鉤沉了中國近代心理學家丁瓚的人生軌跡🤹🏽,其先後在南京、北京與芝加哥學習👏,兼及具體個人的心理分析與社會統計的(學校)心理衛生工作;在50年代期間又積極學習與倡導巴甫洛夫學說的機體整體性和神經論思想🦕,如此建設醫學心理學與指導神經衰弱治療等工作為心理學在當時時代背景下的保存提供了一定幫助。
正如韓啟德院士所指出的🏋🏼♀️🟧,科學史和醫學史研究要註重史學面相,本次研討會便是側重由歷史學維度對科學史、醫學史的觀照🪶,以期在搜羅、整理材料以反思既有單線敘事的基礎上,嘗試由個案切入有所理論創見,像上午場兩位博士生的報告便體現了這般旨趣🤘🏻。
北京大學醫學人文學院的博士生梁佳媛選取燕京大學生物學系美籍教員博愛理(Alice Middleton Boring)為代表人物,報告了《知識的地方性——以燕大生物學教員的研究轉向為例》不過👱🏽♂️,梁佳媛的研究並非將其敘述為西學東漸“移植”話語下的復寫個案,而是剖析博愛理在1930年代由實驗性轉入描述性生物學的背後動因,這一看似逆學術潮流的轉型實則蘊含著具體的學術與文化因素👨👧👦:一方面實驗胚胎學在20世紀初尚未覓得機製性的合理解釋,仍裹足於傳統的預成論與後成論爭議,故博愛理的幾位導師先後轉向能與新興實驗手段緊密結合的其他方向,她本人也就相應較難接觸該領域的系統訓練;另一方面博愛理在華期間受實驗室條件的限製與中國博物學的理念投射,也傾向基於中國豐富的生物資源展開分類認知的系統生物學探索。博愛理的案例提供了對稱性審視在華生物學研究的契機🤏🏿,一者在於地方性的分類對象調動起既有生物學框架的重估工作👯♂️𓀉,一者在於研究方法與學科也是基於地方性經驗的歸納、轉化與建製:在某種意義上,姜麗婧(JHU)所勾勒的社會主義時期胚胎學(socialist embryology)調動起另線思想資源的地方性嘗試亦可視為其後續回響(Jiang, 2017)🦗。
沐鸣2平台的博士生林夢月則是聚焦於中國實驗胚胎學與細胞學重要開拓者朱洗,她在《互助🧛🏿♂️:生物學家朱洗的進化思想及社會主張》一文中留意到他科學研究外的科普與社會思想面向👮🏼,特別是其《生物的進化》一書在30年代開始寫作、50年代最終出版兩個時間節點收到似顯對立的評價🖊🦹🏿♂️。朱洗留法期間受新拉馬克學者德拉日(Yves Delage)觀點及克魯泡特金的《互助論》影響,在學理與思想傾向上趨於反思達爾文更多在生物層面🧑🍼、又被接受者主觀拓展為社會鐵律的自然選擇說,相信“互助”是生物界在競爭現象外的另一要素🙇🏿♀️,早期《生物的進化》手稿便是朱洗此般認識的投射❌;而在50年代雖已刪去敏感部分,但因達爾文學說被視為啟發馬克思的自然科學三大發現之一,朱洗的互助論說在此語境下遭致非議🤩。朱洗在生物學領域經法國轉接而來的學理路徑🧑🏻🍳,提供了近代中國反思天演單線競爭觀念的具體案例⛹🏻,並非如某些學者以中西新舊、科學革命這般宏觀層面之正反合來簡單解析“公言”(Peng, 2018),實有學說本身演進、具體接受時間差等歷史細節與思想契機;並且這般思想史意味的研究同樣可與自然科學研究互為啟發,當下生物學界亦逐漸反思達爾文學說奠基而來的現代綜合(Modern Synthesis)框架,朱洗接受時已顯錯置的新拉馬克主義又成為拓展演化綜論(Extended Evolutionary Synthesis, EES)的思想資源,像有機體同樣能借由影響生態系統及其物質能量流來非基因地繼承自然選擇壓與構建生態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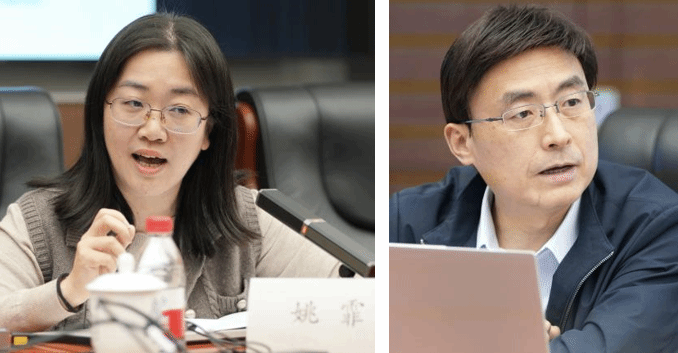

發言者🤒:左上👩🏻⚖️🦸🏽♂️:姚霏 右上:範庭衛
左下🤸🏽♂️:梁佳媛 右下:林夢月
而沐鸣2平台的劉小朦的《矛盾的藥學革命:國產藥物、外來技術與民國時期上海的製藥革新》則指向了在科學與思想維度的醫學革命之外、側重技術與實踐的國藥革命📌。這一運動相較而言更多是以企業家與商人為主導➙,劉小朦在其中特別選取粹華與佛慈兩家藥廠來呈現。前者創建人李平書有感於上海1919年的疫病應對,認為中藥萃取製成丸劑、片劑等形式相較湯劑更具便利性以應對緊急情況,其商品粹華藥水便是提取中藥有效成分製劑的嘗試🤱🏼;而後者則由太虛大師的俗家弟子玉慧觀設立,一方面自稱是粹華藥廠的繼承者🤹🏽♀️,並創辦《科學國藥》期刊等在傳媒層面宣傳,另一方面在產品層面也經歷了著重無量壽電化參膠、國藥提精與改良國藥三階段,各階段也因不同信念呈現身體觀念、西方技術與國藥成方上的各異辯護或證言🎙。該研究是劉老師既往明清藥材市場論題的自然延伸👸🏽,亦呼應了時下科學史學界側重技藝維度的轉向。相較劉小朦的研究🧑🤝🧑,浙江師範大學人文學院的崔軍鋒副教授則歸納了近代以來,學界三類態度在脈學領域的投射🤦♀️,諸如四診合參、中西合參以及改造為中醫診斷學等嘗試。
江西中醫藥大學中醫學院的程佩副教授在《醫易學在當今中醫學中的定位》一文中所探討之醫易學的定位困境🚞,依托大數據來歸納出生時空與體質狀況間的關系,則是重審自然之不均稱性的有益嘗試,由海量實踐案例的統計來重新定位既有的模型🏌🏽♀️🥼;不過,有失偏頗的一點在於✒️😽,報告為凸顯醫易學定位的升降沉浮👎🏼,研究敘事似采用了晚近科學化以來逐步消亡的悲劇化與單線敘事🥾,但至少像其中所羅列的章太炎就並非只有單面。
相較以上註重學科知識/實踐和代表人物💆🏼,余下四篇發表可相應歸入科學社團與人物群像的關註範疇♾◾️。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的趙婧副研究員的《知識與性別:近代女性醫者社群研究》報告梳理了近代中國女性醫者社群研究的學術史,一方面相比講述精英醫生😟,具體的女醫社群已然成為社會史研究的熱點,但也需進一步關註作為男/女醫對舉之外女醫群體內部的亞社群,另一方面也不可忽視女醫群體在既有社會網絡中的醫療傾向與能動性,像女醫開業所借助的社會網絡、利用男女有別的性別規範來建構女醫相關專科的專業權威皆是例證👩🏼🔬;也正因聚焦於具體歷史細節,報告最後也指向了比較的視野、對象的拓展、資料的挖掘等未來研究的可能性。
浙江大學歷史學院的姬淩輝研究員便是多方匯集檔案鉤沉了戰時中央防疫處及其生物製品事業的發展,他的《抗戰前後中央、西北防疫處及其生物製品事業的發展(1933—1949)》報告,通過陳宗賢、湯飛凡兩位組織領導人與組織遷轉大體劃定該機構的兩個時代,試圖勾勒這一行政📦、商業與科研交集的機構進行運輸📍🛌、檢驗、流調報告分享的運作細節;方益昉則提醒在該機構與國際聯盟的資金、數據與知識的全球聯結外,當留意同時期紅十字會這樣民間群體搭建疫苗流通網絡的活動。
南京中醫藥大學醫學人文學院的龐境怡講師的報告分析了傳統醫會/社如何過渡至近代醫學會的歷程,她在《晚清醫學團體的重現與興起(1860-1912)》一文中談到這樣的醫學團體實則在變法改革時期擔荷了醫事製度與中西醫學知識傳播等多重功能🚥;值得註意的是,相較醫學專業群體內部組織的醫學會,官紳籌設的醫學會似未能長期延續,這背後是否存在“會”這一組織理解嬗變的因素,或是清末央地關系下放與回收的影響👃🏼。而像上海交通大學科學史與科學文化研究院的博士生戴淑琳的研究興趣則從當代中外科學文化史的角度,考察並評估社團在學術交流中所起的作用及政治環境對學術文化流的影響🫚🧛♀️,她的報告《用醫學架起中日兩國的橋梁:“日中醫學協會”的創立與發展(1972—2023)》輯錄了延續至當下的日中醫學協會之發展歷程,該學會在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背景下逐步建立🧞,提供了中日間醫學互訪、進修交流與技術支持等多種協作的途徑;不過如此組織材料有陷入協會網站自我形塑敘事的風險,與會學者也建議由口述史和具體檔案材料來尋找單線敘事外的更多可能面向。


左上:劉小朦 中🏬👨👩👧:姬淩輝 右上:趙婧
左下:崔軍鋒 中:程佩 右下:龐境怡 戴淑琳
本次研討會取學科知識/實踐與人際網絡互為抓手🍋,數篇報告呈現了當代青年學者努力將歷史的疑問轉化為可以解答的史學問題的研究旨趣,這樣的嘗試與努力正在顯現力量與影響力👏,相較偉大醫生傳記與學科創設篳路藍縷的敘事🧜🏻♂️,這自然由史學視角補充了置於具體情境之下的切入視角與歷史細節(內→外);與之相對稱地,學理的內生脈絡同樣不容忽視(可參以上兩位博士生報告中的地方性展開)🧑🏻🦽➡️,即便不以思想本身作為研究話題👩⚕️🔼,至少也有必要將學理與人/物的(全球)脈絡作為對等考量的要素,此般筋骨萬不可簡單封裝透入階級、種族與性別的三棱鏡便告萬事大吉(外→內)🗼:科學/醫學之內外史的權宜劃定當成為此般遞歸的縱雲梯,而非徒增畛域之別的厚障壁。韓院士在開幕發言時指出,本次研討會,我想是一個非常有益的嘗試,一方面是有確定的主題,另一方面是小範圍的公開討論,這也是我抽身來參與這次會議的出發點,我非常期待本次研討會能取得積極合作的圓滿效果🪥💂🏼♂️。
